从富强“本末”观到文明“本末”观
王阳明所说的“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币观。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解释了“本末”二字合用的依据。
从先秦开始,“本末”一词便大量出现于关涉治国理政的言论中,其指涉对象具体可分为二:一是治国的方略、政策币观。二是经济领域的“本业”“末业”之分,前者对应农桑,后者对应工商。
晚清以降,随着国门被打开,时人开始正视西方国家的强大富庶,并寻求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币观。从当时很多人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沿袭了传统的“秉要执本”观念。
有论者认为,近代人所说的“本”指传统的“道统义理”,“末”指军事经济技术和制度;实则这二者在当时所指向的外延不断变动、人言言殊,不可一概而论币观。但他们大都主张要学习西方国家富强、文明之“本”,从而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最终实现国富兵强。
因此,无论守旧者还是革新者,大都以“本”来为自己的主张正名,以突显、强调其正当性和重要性币观。而这种观念,显然也是与传统的“崇本抑末”“重本轻末”思想遥相呼应的。
随着时人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和了解不断深化,其“集现代文明与帝国强权于一身”的双重面向被言说者普遍接受,他们也由此确立了“富强”“文明”的目标币观。
一、富强“本末”观和文明“本末”观
1.富强“本末”观
晚清守成主义者延续的是正统儒家思想,即所谓“富民”“教化”思路币观。自鸦片战争之后,时人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方在武力上的强盛、商业上的繁荣,这种寻求富强的发展道路极易使人联想起法家所倡导的“富国强兵”。
基于这种认识,“过去受压抑的法家耕战思想被重新‘发现’”币观。洋务派以此为依据,对守旧者所持的儒家正统立场展开指责、批评。他们的主张也不自觉地从儒家立场逐渐滑向法家立场,王韬所说的“富强即治之本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展开全文
当时中、西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巨大落差,使洋务派开始批评不重视“器物”和“技艺”的传统理念币观。左宗棠指出:中、西之间,一个以“义理”为根本,一个以“艺事”(即武器、科技)为根本。洋务派反复强调武器和制造等的重要性,并把它视作西方富强之根本。
随着人们留意于西方工商业的繁荣昌盛,重农轻商的“本末”观也开始被反思、否定币观。在古人观念中,农业是“本业”,工商为“末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历代统治者也基本延续了“重本抑末”“贵本贱末”的政策。
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声音,如苏轼的“农末皆利”、郑至道的“士农工商皆本业”、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等思想,试图将二者等量齐观,但均未得到广泛认同币观。近代人则从根本上颠倒了农业、工商二者的位置。
有论者所说的洋务运动“对传统的‘本末’观念进行了冲击”,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币观。与这种观念相伴而生的,是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转向“重商崇利”。
李璠认为西方国家都是以经商作为“立国之本”币观。他们进而呼吁政府讲求商政,郑观应主张“备有形之战(指兵战)以治其标,……裕无形之战(指商战)以固其本”。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派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在上述领域的领先地位,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出必须要学习效仿的结论币观。因为依照传统的“道”“器”观念,西方再强大,也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
“船坚炮利”、工商兴盛,这些只是“术”“器”,并非“道”币观。“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
在这种表述中,言说者有意识地将西方“富强之本”降格为“术”,并将其定位于中国自强举措之“末”币观。因此,时人尚能乐观地面对中西在“器物”层面的差距,并用“机运”等观念来自我宽慰。
这也说明当时的言说者对于中国文明深层的精神内核(“道”)充满了自信,李鸿章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币观。他们更进而质疑、否认西方国家存在“道”。
张树声认为西方“礼乐教化,远逊中华”,“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予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币观。既然中国的学术思想、伦理纲常无不完备,所以只需要吸取西方“制造之长”以弥补中国的不足即可。
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语,可视为洋务派的普遍看法币观。
当然,也可以认为洋务派的这种贬抑不乏策略性考虑,因为如果在“道”“术”两个层面同时肯定西方,必然会招来更多的反对声音(如“用夷变夏”),其变革主张便无法落实币观。
“礼失求诸野”“西学中源”等说法的提出,似亦有这种考虑在内币观。有论者指出:“洋务派以‘西学中源’说为由,抵制顽固派的阻挠,……实行‘自强运动’。”
2.文明“本末”观
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时论大都倾向于将战败归因为洋务派未能真正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币观。
同时,随着当时人对西方了解的逐步深入,以及欧洲“文明史学”经由日本输入中国,再加上甄克思、福泽谕吉等思想资源的传入,“文明”一词频繁出现于当时的报刊中币观。
与之相随的,是西方不再被视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方浚颐语),反而成为文明的象征币观。时人常使用严复《原强》中的“文明国”“开明之国”等词来指称西方,“欧洲文明神髓”成为已退居至“半开化”的中国所要了解和学习的对象。
有论者认为:与传统观念相比,这种“以西洋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可称为“逆向的天下主义”币观。梁启超将文明细分为“形质之文明”和“精神之文明”,并强调“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
知识阶层所议论的话题,也渐由物质层面转移至精神层面,许纪霖认为当时人所看重的议题,从“器”“技艺”转变为“德力”“智力”等人本身所具有的素质币观。在这一舆论氛围下,知识阶层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教育、政治等话题。
有论者指出:“在戊戌启蒙思潮中,文明的范畴超越了器物层面,制度文明占有重要位置币观。”到了1910年,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仍用“政治修明、教育发达”来形容西方国家。
有意味的是,当时的确出现了将政治归类为“精神文明”的言论币观。如《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指责当时的外交官、留学生所理解的“西政、西学”不过是“船械之坚利而已,制造之精巧而已”。
“举物质之文明而津津道之,于精神之文明固未尝梦见也”,并明确提出“民权为致强之本”币观。
维新时期有关政治的言论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风气、政治制度币观。郭嵩焘说:“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并指出:“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二是议会等政治机构的设置币观。有人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在于教育、学问知识。
严复《论教育书》明确提出教育是“强国根本”,因而“根本救济,端在教育”币观。但是,具体到应该以哪一种学问知识为主,言说者之间存在观点分歧。
李端棻重视关于治国要义、“富强之原”的知识;张之洞认为每个国家各有其擅长的学问和礼仪制度,这是各强国的“本原”;李善兰则将其具体化为“算学”币观。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洋务运动相比,维新运动时的言说者更看重西方强盛之“术”“器”背后之“学”,说明对西方的认知较之前已更为深入币观。
同时,此时言说者反复用到的“中学”“西学”概念,暗示出他们对自身的“道”已不复有前人的自信,因而将其降格为“学”,同时又将西方的“术”升格为“学”币观。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也昭示出“道出于二”的事实。
当然,很多言说者不甘心于将这二者并列,便反复强调“中学”的优先地位币观。
维新运动之后的诸多言说者对诸如兴业、武备等的主张见解,未超出前人太多,倒是对政治这一话题保持了持续的兴趣,立宪派、革命派等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一致性币观。
如“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币观。余一《民族主义论》认为:“今日欧族列强立国之本,在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革命派更青睐使用“文明”一词,并与其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币观。在他们看来,中国文明开化时间早,“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但后来“被北方一蛮族所征服,丧失其五千余年圣神相传之祖国”,因而革命派又重新兴起肯定、赞扬传统文明的思潮,并且树立了以黄帝为始祖的中国文明之“统”。
“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币观。”革命派还借用“文明”“野蛮”之分和“夷夏之辨”的观念,将晚清政府贬斥为“满夷”“胡清”,从而消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他们进而以法国大革命等史实为依据,将“革命”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如“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币观。
二、“本末”观论争
回溯中国近代知识阶层的西方认知历程时,可以看到的一个舆论倾向是,时人在将自己的观点主张标榜为西方富强、文明之“本”的同时,也往往会较为严厉地批评其他人的观点主张只能算是西方富强、文明之“末”币观。
这样一种话语逻辑几乎已成为一种“套话”,在近代知识阶层的文章中层出不穷币观。
在甲午战败之后,只有郭嵩焘等极少数人认为洋务运动的举措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币观。更多人则借助战败这一事实展开对洋务派的批评、指责。
宋育仁批评洋务派的做法是“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币观。维新运动倡导者在强调自身主张的重要性时,对洋务派做了更严厉的批评。
此外,还可举出很多类似观点,如张树声、徐勤、钟天纬、李桂林、谢觉哉等的观点币观。
与此相关的,是晚清兴起了要求进行彻底变革的主张币观。其后,革命派同样批评立宪主张是“不知根本上之解决也”。
这些言论反映出知识阶层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都期望抓住西方国家发达兴盛的根本所在,进行学习模仿,并迅速取得成效币观。
由上可见,认识和评说西方文明、比较中西文明,是近现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币观。林语堂《机器与精神》一文所说的“近人好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大题目”,确是实情。
而西方国家展现给近现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形象,也是与当时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同时期的人们看取的是其不同的侧面,也由此形成了对其时而褒扬、时而贬抑的复杂态度币观。
三、总结
综上所述,近代知识阶层对西方国家的认知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在将西方的一切现象视为合理的前提下,重新激活并借用传统思想资源来解释面对异质文明的困惑,表现出主动调适的特点币观。
而当中西差异难以调和时,言说者会主动转变观念,向西方思想观念靠近,并以“文明”来论证其合理性币观。
比如进化论所内含的“竞争”观念,与传统崇尚“让”、反对“争”的观念相冲突,而这些言论所体现出的以西观中、融汇中西、“以今律古”等多重态度的杂糅,以及传统思想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于研究者在今后研究中作更深入的开掘币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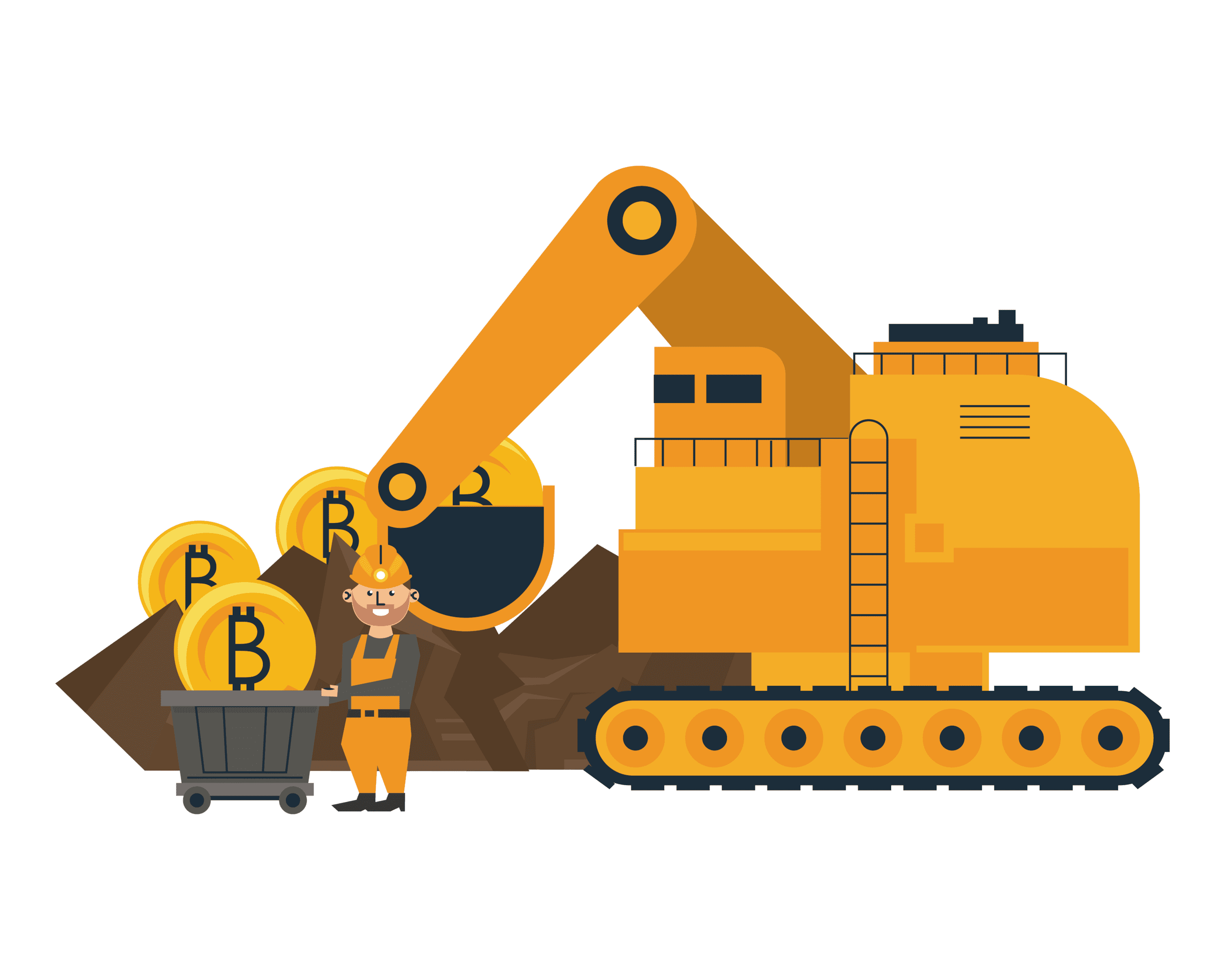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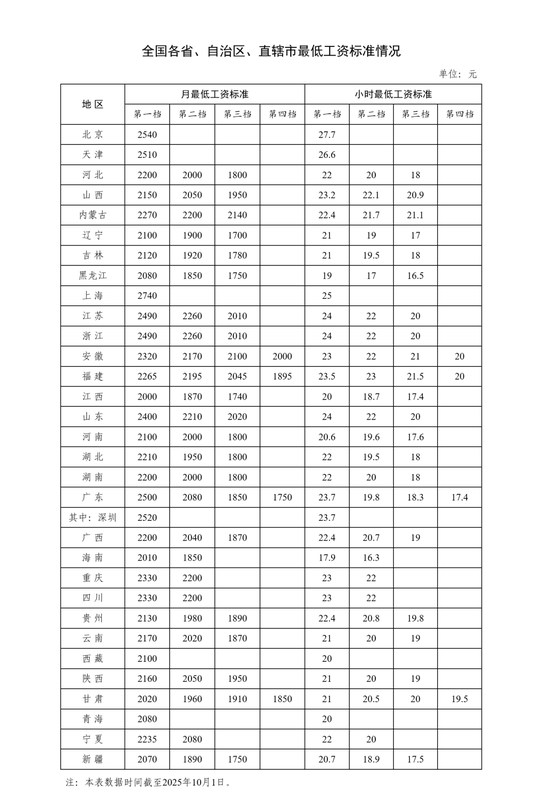



评论